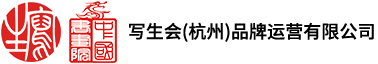-
新书推荐 | 吴佩烔《异域之眼:美国汉学中的中国艺术问题研究》
- 时间:2025-11-27 来源:中国写生会 浏览量:
异域之眼:美国汉学中的中国艺术问题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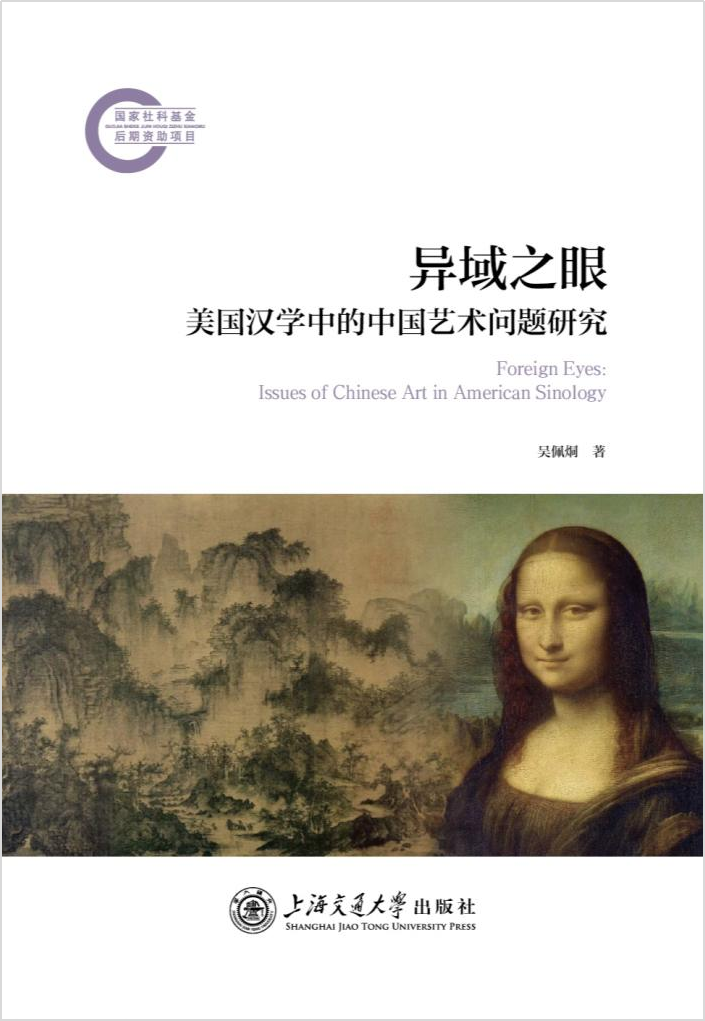
【书名】异域之眼:美国汉学中的中国艺术问题研究
【著者】吴佩烔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ISBN 】978-7-313-33090-1
作者信息
About the Author
吴佩烔,江苏南通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成员,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中国学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等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多项,迄今已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美国汉学视野中的宋代文人趣味》。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与兴趣为:美国汉学、比较诗学、艺术哲学与艺术理论、文学与艺术的跨学科研究等。

内容简介
Summary of Contents
本书从跨文化视角出发,提取归纳了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历程中所涉及的六大基本问题——对于视觉的观念问题、艺术的意义与表意功能问题、艺术与语境的关系问题、艺术与审美意识的关系问题、艺术史家在艺术史叙述中折射的个性审美问题、中西艺术比较研究方法论问题,并以此为线索,梳理美国汉学之中国艺术研究的方法论建构、演变与特点,挖掘其中的西方哲学、美学、艺术学思想背景及其在面对异质文化问题时的调整变形,分析美国学者如何对中国传统艺术问题、观念和作品进行判断、接受、观察、回应、阐发,乃至如何提出和应对跨文化语境中特有的、新的艺术问题,从而厘清这一汉学领域的中西文化与思想互动形态及方式。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绪论:既是艺术史,也是汉学
第一章 以西释中:源于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的中国艺术研究方法
第一节 作为“艺术科学”的形式分析
第二节 致力“人文学科”的图像学
第三节 着眼“外向综合”的艺术社会学
第二章 眼见之证:视觉方法之核心观念与中国艺术的碰撞
第一节 以视觉为中心的内在逻辑
第二节 对图像自律的跨文化检视
第三节 视觉方法中的文本问题
第三章 图像何言:对中国绘画之意义与表意功能的追问
第一节 图像学的再建构
第二节 视觉的主动表意
第四章 内外之辩:围绕中国艺术社会机制的语境主义路径
第一节 西方人文领域的语境主义
第二节 美国汉学家的语境主义诠释实践
第三节 还原与循环:语境主义的诠释学争议
第五章 重新发现:关于中国艺术与审美意识关系的认知演进
第一节 审美意识在艺术史中的地位变迁
第二节 借道画论:重审艺术中的审美意识
第三节 “新艺术史”背景下以旧生新的多元阐释
第六章 述者亦作:作为域外中国艺术史家的个性审美表达
第一节 艺术史叙述中的艺术批评:艺术史家的主体性表现
第二节 艺格敷词的复活:艺术史家主体性的语言表征
第三节 以“生命力”为关键词的审美趣味
第七章 交会之思:中西艺术比较研究方法论探索
第一节 从张宏的山水画到兵马俑:中西艺术影响研究的尝试
第二节 中英图像的政治视觉:中西艺术平行研究的尝试
第三节 比较视域中的“书画同体”:使中国命题成为共享视野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本书所涉及汉学家中英文姓名对照表
索引
跋
书 摘
绪论:既是艺术史,也是汉学
当代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艺术进行的跨文化观照和艺术史书写,除了围绕中国艺术史中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事件和艺术家等而产生独特洞见、误读乃至争论,也在中西跨文化语境之中触及了一系列艺术理论和艺术研究方法论层面的基本问题,构成了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视域下的问题维度。笔者将从这一视角出发,以当代美国汉学界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跨文化观念碰撞与方法调整为关键线索,以对美国汉学之中国艺术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梳理为基础,探究这些问题呈现于该领域的由来脉络、相应的处理方式和其中的中西跨文化艺术认知机制,厘清当代美国汉学在艺术领域体现的中西文化互动形态。
作为美国学术界的一门学科,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成型于20世纪中期,并一直持续至今;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中国传统绘画、书法、园林、器物装饰等视觉领域,以及在这些门类中作为艺术活动主体和文化主体的相关艺术家。这一领域是中西跨文化交流的典型之一,其中涌现了相当一批重要学者和大量著述,成为这一时期西方研究中国艺术的主力,并在海外的中国艺术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艺术史研究视野的全球化,不但当代美国学术界的中国艺术研究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方面得到长足发展,他们的成果和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逐渐得到国内艺术研究领域的注目乃至重视。出于各种动机,除了译介他们的著述,通过展览和学术会议等形式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国内学者也在对中国艺术史论问题、艺术作品分析评判、艺术家相关问题等的研究中,引用和参照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海外学者观点、成果乃至研究方法,并与他们展开讨论与争鸣,逐渐形成一种围绕中国艺术而展开的世界性学术交流图景。
然而,要让世界性的艺术视野真正得以确立,让跨越性的艺术交流对话以真正可行的形态、路径、方式展开,让真正具备跨越性的意义得以在对话中生成,就必须处理好对话双方的关系,形成合适的对话平台。此处的跨越性,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跨越重洋与国界,还意味着文化空间的跨越,即需要跨越不同文化、民族、语言、艺术经验等的重重界线;而跨越界线的前提,又是对作为视域出发点的各方自身身份和视域的确认,此后方能确定各自视域的扩展路径和范围,并在由视域扩展和相遇而形成的交集空间之中,构筑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交流场域。相应的对话交流和言行反应,都包含着意识的距离:他人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相互碰撞之处,既有因为视线的旅行和视域的扩展而与自身原点产生的距离,也有他人意识与自我意识二者之间的距离;在由这双重距离构筑的空间中进行认识与价值的交换,产生相应的交流成果,也就是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说的“精神不在‘我’之中发现,它伫立于‘我’和‘你’之间”。要在考察这类对话交流活动时把握这种意识的距离,就使得确定自我和他人的身份以及位置成为一个微妙但又重要的问题。那么,当我们在接触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阐释成果时,在作者姓名一栏中看到高居翰(James Cahill)、卜寿珊(Susan Bush)、包华石(Martin J. Powers)、何慕文(Maxwell K. Hearn)、李嘉琳(Kathlyn Maurean Liscomb)、孟久丽(Julia K. Murray)等名字,看到他们中英文姓名兼有的具名方式,我们又应当如何定义他们在相关研究中的身份和位置?
一种定义是将他们的研究归入传统意义上的海外“汉学”(sinology),或使用二战后在美国开始兴起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一词,而他们的身份自然也就是“汉学家”(sinologist)。所谓“汉学”,顾名思义即“外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首先强调的是由西向中的跨文化特征,兼及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学科领域特征。例如2001年出版的《北美汉学家辞典》,将“汉学家”定义为“从事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收录了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领域在内的五百余位相关学者。只要认定艺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以中国艺术研究为学术生涯主要方向的美国学者自然可以置身于汉学家之列。作为非华裔的外国学者而拥有一个中文名字,在今天仍是强烈体现汉学传统的一种做法,是汉学家身份的典型标志之一,高居翰、卜寿珊、包华石等也不例外;而且这些中文名字在起名时多显工巧,既在读音上保持与外文原名的联系,又能在中文语境下显示文采,成为跨文化身份的最明显符号。
不过,翻开《北美汉学家辞典》中各人介绍的“研究范围、专长”一栏,我们又能看到其中蕴含着另一种身份定义:
卜寿珊:“东方艺术/印度,中国,日本”
高居翰:“艺术史/中国与日本/中国画,日本画”
何慕文:“艺术史/绘画,书法”
李嘉琳:“艺术史/中国明代至今/绘画(包括收集及赞助)艺术理论的历史的及 批判的作品,绘画主题与艺术品装饰间的关系”
孟久丽:“艺术史/近代/中国/绘画中的插图与其他绘画工具”
包华石:“艺术史/战国,汉,宋/绘画理论,艺术与政治”
这些介绍之中又蕴含了另一种身份与位置定义方式,即以学科为界。这些学者并没有像比较文学等典型的跨文化研究学科那样,将跨文化作为其研究中的一个外在着力点和强调特征(虽然从学理上而言,其中的跨文化语境不言自明),尚未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将中西两种文化主体并立的架构,而是看上去相对单纯地以艺术史学科中的中国艺术史(或其他国别艺术史)以及某些分支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在大多数场合和研究文本中,从事中国艺术研究的当代美国学者既没有在字面上强调自身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是作为一种他者意识而活动,也不强调中国艺术相对于他们的自我意识而言是作为一种他者而存在,不将自己的研究列为借助对异质文化的描述、诠释而巩固或反观西方自身的文化政治。如此便给出了另一条定义他们身份的路径,即定义为“艺术史家”而非“汉学家”。
这一路径也正是国内对美国学者的中国艺术研究进行关注和论说的最主要方式:在艺术史学科自身的视野和架构之内,围绕双方均涉及的中国艺术史具体问题而展开论说与争鸣,作为纯粹的艺术学问题来处理;将参与其中的美国学者作为比较单纯的艺术史专业学者来看待,与他们通常以“艺术史家”作为自我定位、极少以“汉学家”自称形成某种默契。这也与影响到当代美国学术界之中国艺术研究方法架构的一个重要事件——20世纪中期的“汉学还是艺术史”之争有关。随着成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的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及其研究方法论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领域,围绕艺术与整体性历史框架、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事关艺术与人文领域的关系),以及艺术和相应跨文化语境、跨文化方法之间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接受现代西方艺术史专业训练的学者与这一时期的汉学家之间爆发了根本性的争论,并导致艺术史家身份与汉学家身份之间、艺术史专业方法与文化史方法之间形成对立。由于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建立于西方理性现代性思潮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现当代历史语境中对理性和科学等现代性价值的追求,我国学者也倾向于以更具现代性色彩的“艺术史家”身份、而非自“前现代”的近代早期延续至今的“汉学家”身份,看待从事中国艺术研究的美国学者。此时即使仍以“异域视野”“汉学界”等语汇指称他们,也只是代表这些学者所处地理空间层面的意义,不再强调其中的跨文化意味,并且仍以现代艺术史学科定义下的专业性眼光与他们展开交流探讨。
然而实际上,依旧可以用“汉学家”三个字代表的跨文化身份,相应地“以西释中”的跨文化路径,乃至于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方法自带的“西方性”,从未真正被排除在学术意识与话语表达范围之外。在国内艺术界和研究者论及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艺术的方法论时,多少能看到对于他们的各种疑虑或隐或显:对于他们具有“西方性”的方法观点,对于他们是否真正摆脱了自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乃至这些西方学者是否真正可能做到“懂中国”“懂中国艺术”——特别是在海外学者所提出的观点具有强烈争议性之时。美国学者自己对这种情况亦有所意识,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保持着取中文名等典型的汉学家行为方式,实质上依然保留了对“汉学家”身份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来自中国的、基于文化视角的批评性反应,比如高居翰在其《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The Compelling Image: Nature and Sty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的中文版提到了这种状况:“有些中国同事对我说,以他们对中国出版物的了解——远远超出了我有限的中文阅读水平——来看,国内学术界仍在很大程度上拘泥于文本研究,而忽视了视觉研究的方法,以为只有那样才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而所谓‘风格史’研究则源于德国,从根本上是西方的,不适用于中国。”他也提到自己的观点所受的类似批评:“其中甚至有一位评论者认为这是‘东方学’(Orientalism)的幽灵复现,也就是认为我用了外来帝国主义的价值观点与诠释法,强制地套用在中国本土传统之上。”
这些表达中所涉及的一些艺术理论问题,如视觉与文本、传统与现代、风格史的适用性等,都具有复杂内涵,不能以单纯的东方西方之分一概而论(一些将在本书中论及)。但能够产生这样的争论,便意味着相关问题已经跨出了艺术史学科自身的专业范畴;可以用“汉学”二字表达出来的跨文化语境、跨文化身份和跨文化方法问题,依然是考察当代美国学者的中国艺术研究时所不能忽视的内容。他们的研究是对中国艺术的跨文化阐释,依然属于一种汉学研究,是当代美国汉学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围绕中国艺术史具体问题的讨论以及对于观点正误、研究水平的争鸣,而是以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与艺术视域交流碰撞的宏观视野展开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美国汉学对中国艺术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演进,既与西方艺术史学科方法体系发展和艺术史书写方式演变保持总体相符的方向,也与这些背后的西方文化理论和文艺美学思潮发展演变相互呼应;既符合20世纪后期美国汉学从“西方中心”到“中国中心”、向语境主义和多元主义文化方法论转型的背景,也逐渐超越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为其奠定的学科框架、体现美国汉学(以及整个海外汉学)作为来自异质文化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具有的科际整合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美国汉学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不是一个封闭的艺术史学小圈子。他们的研究虽然主要以中国古代艺术家、传统艺术品和艺术话语为载体,但所反映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对中国艺术本身的感知、评析、考据,其本质是运用中国的图像材料和相关文本,书写域外视角下的中国艺术史与文化史,所以更在文化观念和思维层面构成了两种异质文化体系和艺术观的直接遭遇与对话。他们的研究是在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坚实支撑下,对中国艺术展开相对于中国传统视角而言的异域关注,进行相对于西方经典范式而言的新式书写;于是,既为中国艺术史研究自身贡献了问题意识、视角、方法、材料与观点,本身也是一种西方背景下的艺术文化行为,构成这一时期西方艺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艺术研究的文化属性,突破只从纯粹的艺术史学科角度来关注对中国艺术的异域论说的局限,寻求更为广泛和更有深度的研究样式。在对当代美国汉学之中国艺术研究的考察中,我们固然可以,并且应该继续就中国艺术和艺术史的具体问题,与海外学者进行交流、探讨乃至争论,关注他们言说和表达的内容,评价这些内容的正确性、合理性、适用性;但我们更有必要深入剖析这些研究背后所体现的中西艺术观念、中西审美意识解读与交流,还原在这些根本之处所生发的问题意识、产生的复杂碰撞与展开的深刻互动,考察他们在这些过程中的价值观念取舍、观看方法选择与构建、概念范畴接受与阐发等,探究他们鉴析中国艺术和书写中国艺术史之方法的成因、演变过程以及思想文化观念根源。通过从了解“他们说了什么”到探寻“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才能够更好地揭示中西美学和艺术文化观的交集所在、异质之处与互动互适之道,并有助于相互认识与相互交流的推进。
正因如此,这一系列问题还属于一种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层面的问题。所谓“诗学”(poetics),即便在古希腊时期也并不单指诗歌之学或文学理论,其中也包含了阿伽萨耳科斯(Agatharkhos)、欧弗拉诺耳(Euphranor)、阿培勒斯(Apelles)、普罗托革奈斯(Protogenes)等艺术家的著书立说,以及纳入了对修辞和艺术理论的专门研究;为西方文论奠基的亚里士多德《诗学》,同样牵涉到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故自此开始,“诗学”便已成为广义的文艺理论的代名词。以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的广大视域对各国文艺理论进行汇通性研究的比较诗学,实质上早已不限于文学研究,而是将哲学、艺术、文化研究等诸多方面的理论视域和问题意识纳入自身。当代美国汉学对中国艺术展开研究时所牵涉的各种深层问题表明,他们运用中国的图像材料和相关文本,书写域外视角下的中国艺术史与文化史,也在比较诗学层面构成了两种异质文化体系的遭遇与对话。以比较诗学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方法路线,对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加以剖析,便具有了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由此出发,笔者的根本思路是紧扣跨文化和跨学科这两个关键点,把美国汉学家的中国艺术研究同时作为一种文化史书写和比较文化研究,视为一个中西哲学、美学、艺术文化观念等相互交流、碰撞、调整的过程,经由两种文化在中国传统艺术问题之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砥砺互动,更加深入地把握中西艺术文化观念的内涵,把握双方对艺术问题所反映的人文学科特质及其内部关系的理解,把握它们在深层的共通处与异质性,并可借此反观中西双方的艺术文化构造取向。与之相应,笔者的基本方法是:梳理当代美国汉学家之中国艺术研究方法论的建构、演变与特点,挖掘其中的西方哲学、美学、艺术学思想背景及其在面对异质文化问题时的调整变形,分析他们如何对中国传统艺术问题、观念和作品进行判断、接受、观察、回应、阐发,如何提出和应对跨文化语境中特有的、新的艺术问题,从而厘清这一汉学领域的中西文化与思想互动的形态及方式。
从当代美国汉学在中国艺术研究领域所走过的数十年历程中,笔者提取了以下六大基本问题,作为切入和考察其中之跨文化砥砺互动的窗口:
(1)对于视觉的观念问题。当美国汉学家对中国艺术进行视觉上的考察,特别是运用所谓“视觉(visual)方法”、进行各类视觉研究时,其中很多时候已然蕴藏着西方对于视觉自身、对于通过视觉进行的认知活动所具有的基本思想和深层文化逻辑,以及由此形成的根本观念——将视觉置于本体论地位。这一观念脉络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哲学,由康德美学中的无利害静观学说加以承续,下启19世纪后期开始在西方文艺领域兴起的理性现代性思潮——这一思潮又正是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的思想基础。随着这种视觉观念被当代美国汉学继承到跨文化语境之中,势必与中国艺术及其对视觉的观念传统产生碰撞。这一碰撞在两个分支问题上呈现得尤为明显,一为艺术自律和图像自律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艺术,二为对人文领域内最重要的两大载体——图像与文本(text)之间的关系处理。
(2)艺术的意义与表意功能问题。西方传统也并非只将视觉置于本体论的重要地位,长久以来同样存在着类似“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认知与论述结构;当西方汉学进入中国艺术领域之后,也要面对中国传统中同样包含着的对图像意义和表意功能的明确体认。中西文化中同样存在对视觉艺术的人文主题、内涵、功能、地位、价值的认识,使得艺术的意义与表意功能问题成为中西视野交汇的一个重要锚点。
(3)艺术与语境(context)的关系问题。西方文艺研究领域长久以来对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内向观”与“外向观”的划分,本质上即对作为某种话语(discourse)之艺术与其语境关系的两种基本回答;将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与创作主体(文学家、艺术家等)、地理与人文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思想观念等因素联系起来的“外向观”和“外部”研究,特别是作为现当代艺术研究支柱之一的艺术社会学,即以艺术与其语境相结合作为对这一关系问题给出的答案。另一方面,当代美国汉学在观念与方法论层面上的诸问题,本质上也都可以视为跨文化而造成的语境问题,因为各种认知和诠释都不可避免地以文化语境为先决条件,各类“误读”、碰撞、挑战、调整的源头,亦在于中国艺术本身之语境与异域眼光所暗含之语境之间不可避免的错位。当美国汉学家以社会机制为主线并综合其他层面,不断竭力扩展对中国文化语境的探索广度与深度,试图为对中国艺术的诠释寻找更充分的支持,亦是试图以直面语境这一对象本身的方式而加以应对。
(4)艺术与审美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艺术研究的一大基本问题,艺术与审美意识的紧密关系看似常识,但在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的建立发展过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却隐伏着重重张力,产生了不同观点和处理方式:既有将二者区隔切割的要求,也有在对审美意识问题的回避和淡化中保持二者的微妙关系,还有“新艺术史”潮流中重新关注与发现审美意识的主张。当美国汉学家以西方艺术史研究路线为基础、以中国传统绘画为主要对象展开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便会在艺术与审美意识问题上遭遇中国传统艺术史观的独特性及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倾向,从而使得这一问题在跨文化语境下显现出新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维度。
(5)艺术史家在艺术史叙述中折射的个性审美问题。不同于艺术家自身或艺术批评家的审美话语,艺术史家的审美主体性及其在艺术史叙述中的呈现方式是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建立以来的一个微妙问题,这是由于主观性和感性的在场与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所遵循的客体定位原则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但是,一方面在西方艺术史领域也存在认识到艺术史家的主观性、并试图将艺术史与艺术批评融合的观点,另一方面随着艺术史研究和书写逐渐跨出单一文化的藩篱、开始向异域和异质文化中的艺术对象拓展,随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历史传统和视觉语言体系的碰撞,艺术史家自身主体性的活动和呈现空间也开始得到一定的松动,使得上述问题得以凸显。
(6)中西艺术比较研究方法论问题。以在跨文化研究中已经具有相对成熟体系与范式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学科作为参照,当代美国汉学界之中国艺术研究虽然体现了充分的跨文化性质,但总体上还属于艺术史学科框架下一种单向的阐发研究,自身作为跨文化研究的意识和跨文化结构体系还是非常不充分的,尤其表现为既缺少针对中西之间可能存在的直接接触交流而进行的影响研究,也还没充分上升到不以直接接触交流为先决条件(乃至处于不同历史时空)、但可以以比较方法为基础并围绕某些会通性的问题与价值而展开的平行研究。不过,与比较文学学科相对应,在西方艺术史学界和中国都出现过“比较艺术学”(comparative art)或“比较美术学”的提法,相关的比较意识与比较方法也多多少少在美国汉学之中国艺术研究中有所体现,甚至有尝试中西比较艺术研究的典型案例。作为跨文化艺术研究必然的发展方向,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亦不容忽视。
围绕上述六大问题,本书分为七章。第一章作为展开考察的基础,首先对当代美国汉学之中国艺术研究的学科基本框架形成过程进行梳理;其后,二至七章以每章分别讨论一大问题的方式,对这一学科框架下触及的六大基本问题逐步展开探究,并力图使全书的相关考察形成既有纵向层次、又有横向视野的立体框架结构。在纵向层次上,笔者将按照“方法构建历程——遭遇内在问题——做出调整回应”的层次,由表及里地剖析其中的跨文化碰撞交流过程。主要针对两方面:
其一,艺术研究的理性问题框架和相应学科方法(第一至第四章)。在学理上,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仍然植根于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理性研究框架和基本研究路线,因此笔者首先探究:当代美国汉学家如何以此为基础,建立由基于形式分析的“视觉方法”、发展自图像学的图像意义与表意功能研究、基于语境主义的艺术社会学诠释模式所构成的学科研究基本体系;这些基本体系及其内在的西方哲学、美学、艺术观念和文化思维,在艺术自律、图像与文本关系、图像意义体系与主动表意功能、艺术与语境关系等方面,遇到了哪些在原本文化视野和方法论视野中未曾遇到的问题或挑战(或者哪些固有问题在以中国传统艺术为诠释对象时被放大),当代美国汉学家又对此做出了何种调整与回应。
其二,从艺术研究的理性问题向感性问题的延伸(第五、六章)。对于艺术领域的理性与感性关系,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主要植根于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理性现代性视角,但他们在与中国艺术的接触之中,事实上不会仅限于前述的理性研究视野,他们在中西跨文化语境中仍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艺术感性层面的两个基本问题——艺术与审美意识的关系,以及艺术史家自身的主体性审美;因此,在理性的“以西释中”之外,也必然还会有感性层面的“以西味中”,并且他们需要处理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中西观念碰撞,做出自己的调整和诠释。本书亦对此进行探究。
在横向视野上,本书还将考察当代美国汉学家从以西释中的单向阐发研究到尝试中西会通性研究的扩展(第七章)。对于研究中国艺术时所体现和践行的中西文化关系,当代美国汉学界没有满足于单向阐发研究的形态——以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为基础、在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诠释中进行跨文化调整,而是还综合运用中西艺术文化资源,尝试为中西艺术建立更多元的跨文化关系和进行中西艺术会通性研究。笔者将对这些拓展尝试中的学理问题进行剖析。
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梳理当代美国汉学从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获得了哪些方法(以及相应的观念、范畴等),这些方法及其背后的西方文艺理论、文化思维等为从事中国艺术研究的美国汉学家提供了哪些研究工具,这些美国学者对它们在中国艺术问题上的适用性又做出了何种判断和选择。在学理上,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仍然植根于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后者为前者的基本学科框架提供了三大最主要支柱——以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的形式分析、风格研究为最典型标志的“艺术科学”,以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为代表的图像学研究,以艺术社会学和“新艺术史”潮流为核心的外向型研究路线;前者则与后者的发展进程相呼应,移用其中的学科观念、概念、方法,建立和运用相应的研究框架和范式,从而在与中国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思想的相遇中建立特定的艺术史学科视野、体系、问题意识和阐释。梳理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方法、观念等如何超出西方语境自身范围、进入跨文化语境下的美国汉学领域,是研究美国汉学如何对中国艺术做出阐释、并探寻这些阐释中的跨文化原理与表现的最重要前提。
第二章,透视当代美国汉学研究中国艺术史时最为主流的“视觉方法”、最为强调的“以视觉方法为中心”理念之内在,剖析背后的西方视觉思维逻辑和由此构成的核心观念,以及它们在中国文化语境和中国艺术现象面前所遭遇的挑战。在艺术史学科层面上,视觉方法基于以沃尔夫林为代表的形式分析和风格研究而构建,但其背后蕴藏着将视觉置于本体论地位的根本观念,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经典观念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对于图像自律、艺术自律的预设和对于图像—文本关系的基本看法。但是,美国学者以作为异域他者的中国艺术为依托而对图像自律进行的尝试和检视,却得出了背离其初衷的结果;对于图像-文本关系的基本看法、图文二元对立思维和将文本在视觉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置于次要地位的观念,也在面对中国画学传统的海量文献积累、深厚的图文一体观念、重视文本研究的立场时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本章将对这些检视与挑战,以及当代美国汉学家在其中的反应进行梳理剖析。
第三章,考察当代美国汉学家如何以图像学为出发点、又根据中西跨文化语境有所新变,从而对中国艺术的意义与表意功能展开追问。当代美国汉学界在研究中国艺术的这些问题时,将以人文价值为最终目的的图像学研究方法引入了这个跨文化的领域,并基于面对中国文化、历史、社会语境的研究需要,对以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架构为基础的基本框架进行重构,包括:在图像志的层面收集、整理中国艺术中的各种母题和母题组合,分析其来源、对应的寓意以及构成这种对应的思维模式;以中国自身的文化情境和脉络为根据,对潘诺夫斯基原始表述中的“故事”和“寓意”进行相应的替换;以包括类似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方式在内的手段,论证中国画观者将原始视觉经验指向特定主题的途径,等等。同时,当代美国汉学家也注意到,将图像学的基本架构以及由此衍生的综合研究体系置于中国语境之后,会映衬出一个特殊的盲区——视觉艺术是否可能在艺术主体的有意识运用之下成为一种主动表意的工具,如果可能的话这种主动表意功能又将如何运作;他们在美国汉学的视域中对这一研究方向进行了补充。本章将以前述两种探索路径为线索,对当代美国学者的相应成果加以考察。
第四章,以当代西方人文领域的“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认识方法论、当代美国汉学中的语境主义和情境论趋势为依托,考察社会诠释模式和语境主义方法如何以西方艺术史学科的“新艺术史”(the new art history)潮流为背景,在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中得到应用;并考察当代美国汉学家在这方面如何遭遇“艺术与其语境的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以及相应的一系列艺术诠释学问题,又在这些问题上如何做出自身的反应。涉及的典型案例包括:高居翰在他的《画家生涯》中对宏观语境的具体化和考察艺术家在其中的活动方式进行了尝试,但在艺术社会学与他奉为圭臬的视觉方法之间多少表现出摇摆和犹疑不定;包华石探讨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社会思想史语境以及相关艺术的图解模式,而石慢和乔迅更进一步运用传记性语境主义框架,尝试细化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所面临的宏观与微观语境,重建以中国古代艺术家个体为中心的关系与意识之网,寻求将其与艺术作品和观念形成有效关联并助力于对艺术的诠释,但他们的研究之道在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中仍显独特。这一局面源于语境主义与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特殊学科追求之间的深刻张力,它们在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实践中产生的碰撞也对语境主义提出了各种考验,汇聚为艺术研究中的语境主义所必须处理的根本性诠释学问题,并使得部分当代美国汉学家的相关研究成为在跨文化语境中就此展开的独特问答。
第五章,考察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中如何遭遇和处理艺术与审美意识关系问题。当代美国汉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触及和处理以画论(包括对中国传统画论的反应和建构属于自身的画论的尝试)为重要锚点,既形成了与同期西方艺术史论中相似的微妙性,又先于西方的“新艺术史”潮流开启了对审美意识的关注和重新发现;其后又在“新艺术史”推动下产生新旧融合的多元阐释路径。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在这一问题上不可避免地明显受到现当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的影响,但也并非单向地对后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发展进程亦步亦趋、接受后者范式的单向输送,而是通过跨文化语境形成与之既有呼应关联、又遥相映照镜鉴的诠释,从而在艺术文化领域构成了跨文化阐释与对话进程之中一个值得考察的典型。
第六章,考察当代美国汉学家在研究中国艺术时折射出的个人趣味与个性审美问题。在当代美国汉学家诠释中国传统绘画时,即使是艺术史专业出身的相关研究者们,对中国艺术史的叙述中也包含了更丰富的艺术判断,融合了来自汉学家自身的主观要素,或多或少都有基于自身感性、对自身审美的表达;甚至还有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这种拥有艺术家和艺术史家双重背景的特别案例,对于感性判断、审美表达和自身作为一个艺术批评者的在场表现得最为坦然和显著。在总体上,他们作为艺术史叙述者的主体性表现可以概括为:以“艺格敷词”(ekphrasis)的有限度复活为语言表征,以所谓“生命力”(vitality)为审美趣味的关键词。这些既能反映中国传统的艺术感知思维与西方传统的艺格敷词、中国传统的“气韵生动”等与西方的“生命力”之间的共通之处,也折射出西方文化在艺术领域的根本性前见。
第七章,考察当代美国汉学对于中西比较艺术研究乃至“比较艺术学”的研究尝试。在当代美国汉学界也有少量这一性质的探索,并有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和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训练的旅美华人学者加入其中,以其真正身处中西文化之间的文化身份而对这一探索形成特有的视野。对于这样的研究,本章主要选择三大案例作为典型,由此切入和加以考察:(1)高居翰、班宗华等人以晚明画家与传教士所携带西方版画、秦兵马俑与同期西方雕塑为例,尝试寻找和论证西方艺术对中国艺术可能存在的影响;(2)包华石通过比较中国古代与17世纪英国视觉艺术中的政治言说而运用平行研究的范式;(3)旅美华人学者方闻面向西方环境、观众和读者,阐明作为自己艺术观核心、具有深厚中学底蕴的“书画同体”观,并使之成为中西交融的共享艺术视野。这些案例表明,当代美国汉学界也在试图寻找为中西艺术建立更多元的跨文化关系的路径,而这类尝试无论得出的结论是否经得起考验,都有着值得厘清与深思的跨文化方法论问题。
通过这一系列研究可以发现,美国汉学家对中国艺术的跨文化诠释方法论建构,所表现出的本质特征和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既要使源自西方视角的艺术研究方法适应中国艺术自身的独特性,也要令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译介、研究和传播适应西方环境下的学术学理特点、知性追求、观众需求和观看模式。这在客观上是在构建一种双向适应、相互平衡、并对中西双方都具有开辟视野之功的产物。不过,无论美国汉学家如何注意中国艺术和文化的自身特质、从中国自身情境出发,仍可认为是着落于以下根本目的:通过他们在中国语境和跨文化语境中遭遇的特殊性问题,验证和扩展其对于艺术文化问题的方法与视野,寻求由此反推出某种有决定性、统领性作用的艺术世界观和艺术史演变规律,并更进一步追求具有普遍性的艺术史书写方式,从而能将中国艺术和他们自身都包括在内,并安置于合适位置。
因此,我们也有必要突破纯粹的艺术史学科领域与具体艺术问题的视野局限,跳出对其观点正误或研究水平的单纯评判和争论,整体性、立体化地考察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观念与方法,防止在艺术史研究与美国汉学研究整体之间、美国学者们的艺术史家身份与汉学家身份之间、艺术研究与比较文化研究之间制造出割裂状态;有必要将更多从事和牵涉中国艺术研究的美国汉学家纳入研究范围,并在更为广泛全面的文化背景中,以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野处理美国汉学家的中国艺术研究,将其视为运用异域视觉材料书写文化史和探究人类艺术文化观念的案例,重点挖掘对具体艺术对象的研究背后隐含的中西文化、美学思想、艺术方法的交汇与互动。
结 语
包华石的《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之中多次出现一个名为“欧亚大陆”(Eurasia)的术语。这一术语原本常用于表述一个大尺度的地理区域、历史视域和考古范围,并隐含了这样的内涵:欧亚之间具有整体性联系,欧亚之分是文化层面的人为划分,而非基于自然地理的硬性区隔。比如从地理上看,欧洲可视为从亚洲向西伸入大西洋的几个半岛,传统上以乌拉尔山、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等划分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的做法更多亦出于人为设定;以中亚为桥梁的民族迁徙、围绕中东地区的中世纪史、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等,也一直是欧亚大陆视域下历史研究、考古勘察、人类学研究等的重要课题。但在《西中有东》之中,包华石将这一术语从对地理空间和“作为世界历史中心地带”之历史空间的表达,进一步拓展为对横跨东西的整体性文化空间的重新发现与宏观建构,从而形成为比较文化和比较艺术研究提供合法性、合理性和理解路径的底层框架。比如中国和英国将政治抽象概念在视觉上变得形象化的转义策略,对于双方所具有的共通性,包华石认为:
我们将发现,尽管与政治抽象概念对应的术语和图像的内容在两种传统(英国与中国)里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但转义策略的整体发展——从寓言到见闻录——却甚为相似。这种演进模式揭示了在近代早期阶段,认知限制——因此也是结构性限制,必然在欧亚大陆两端都是有效的,这多少独立于“文化”差异之外。
再如对于东西双方形象化模式在某一阶段的共通性:
可以说,横跨欧亚大陆,中古时期的社会形态拥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就导致了类似的形象化模式。最为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广泛使用宗教教条来取代事实与逻辑。宗教教义涉及的是真理,而不是事实,所以中世纪的画家们对于空间的信息、时间的效应、季节的变迁,或者是植物与动物的物理状态等方面都没有什么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佛教极乐世界的景象,就像一幅上帝坐在其权座上面的绘画一样,也不会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真实世界的消息。相反,这样的图像描述的是一种想象与永恒的真理。
刘东在评议包华石的这部著作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运用这一概念的作用在于挑战了把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截然相分的本质主义僵化观念,对“欧亚大陆”所代表的地理空间、文化空间和文化交流史空间的整体性展开重新认识,从而形成对跨文化研究的宏观理解框架:“我们如果利用‘知识考古’的方法,和‘文化比较’的方法,就有可能切实找出影响的轨迹,从而既在‘并驾齐驱’中见出差异处,又在‘分道扬镳’中见出共通点。唯其如此,我们方有可能既从‘一中见多’又从‘多中见一’,乃至找出‘通分’历史的统一标尺,并且寻觅到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向。”
包华石的著作和刘东的评议,主要还是走在利用知识考古来驱动比较文化研究的道路上,为了论证中西会通性对话的意义而运用“欧亚大陆”这一术语作为纠偏和理解的框架。倘若放眼美国汉学之中国艺术研究的学术史和方法论整体,特别是正式确立学科形态、进入当代阶段以来,他们在总体上还没有运行于这样的高度,而是出于学科观念或自身在研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大多选择了回避直接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乃至更进一步的比较艺术或比较文化研究,转为建构由西向中的艺术史阐发。但是,倘若以作为跨文化空间的“欧亚大陆”视角来看,自福开森在《中国艺术讲演录》中以“在中国,艺术是文化的表达”开篇、并提到“希腊人所谓的paideia,罗马人所谓的humanitas,中国人称之为学或问,意思是通过精神和道德的修养而获得的风度和品位上的提升”之始,即使美国汉学界的中国艺术研究并未大规模延续其中蕴含的知识考古与比较文化思维,而是作为阐发研究而存在和运行,也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从欧亚大陆一端到另一端的艺术文化探险之旅。
在当代,我们通常以“跨太平洋”形容中美之间的各种空间关系,美国汉学界的中国艺术研究者也是循着这一路径往返于中美之间,展开自身的各种考察研究;但是他们对中国艺术的研究所反映的文化空间,仍然处在“欧亚大陆”这一框架之内。美国汉学的艺术研究本质上属于欧洲一侧,这不仅仅因为美国在文化思维、认知方式等位面仍是植根于古希腊、古希伯来文明的西方经典文化的延伸,也可以看到来自欧洲的现代西方艺术史学思想和方法传入北美、帮助美国汉学界的中国艺术研究确立自身的当代架构与学科形态的明确过程:形式分析方法和“艺术科学”学派的艺术史观念沿着“沃尔夫林(欧洲)—巴赫霍夫(由欧洲赴美)—罗樾(由欧洲赴美,且赴美前曾在中国工作)—高居翰等美国本土学者”的路线在当代美国汉学界的艺术研究领域扎根,现代图像学研究亦随着其代表人物潘诺夫斯基赴美的脚步而“移居”美国。同时,无论是西方艺术史研究领域还是汉学研究领域,欧美也始终保持方法论演变潮流的整体性和各种紧密的互动:从艺术社会学到“新艺术史”的历程将欧陆与北美同时交织在一起,美国汉学界及相关学术刊物亦与苏立文、柯律格(Craig Clunas)、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等身处欧陆的同行们有密切的关系与交流。再加上美国学者自己访问东方的脚步,以及与王季迁、方闻等华人收藏家和学者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些都将自欧洲延伸而来、作为研究主体的西方艺术史学科与身处亚洲一侧、作为认知和诠释对象的中国艺术联结在一起。即使不去考虑高居翰等对晚明画家是否受到传教士所携带西方绘画影响的探究尝试、包华石对中国古代和17世纪英国视觉政治表现的平行研究等稀少案例,这些也都帮助当代美国汉学界的中国艺术研究形成一种横跨欧亚的文化旅行样态。
有趣的是,这场围绕现代艺术史学科、在地理空间和学术空间横跨“欧亚大陆”的学术旅行,实际上是在中美同期开始、平行展开,并引发既平行又交错的学术回响。生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国家的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特别是以其中的形式分析、风格研究为核心,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随着巴赫霍夫、贝特霍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阿尔弗雷德·萨尔莫尼(Alfred Salmony,1890—1958)等学者移居美国而在美国的艺术研究领域逐渐扎根,并在日后成为当代美国汉学之中国艺术研究学科范式的基础。与此同时,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术和文化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随着持续的西学传播和新文化运动,徐悲鸿、刘海粟、滕固、蒋彝等人也在对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理念和方法的接受和吸取之中,尝试建立中国的现代艺术理论和现代形态的艺术史学。比如当巴赫霍夫等人作为艺术史专业学者的视角逐渐开始引发与早期美国汉学家之间的争议之时,师从德国艺术史家奥托·屈梅尔(Otto Kümmel,1874—1952)的滕固也正在将西方意义上的“风格”概念、此时在西方影响最大的风格研究范式等引入中国,并在《唐宋绘画史》等著作中运用受到李格尔和沃尔夫林影响的艺术史方法,界定风格和划分风格发展阶段。可见,现代的艺术史学科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别开始了从欧洲横渡大西洋和前往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旅行,并分别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社会历史语境中接受审视与提问,以及在不同阶段得到不同的差异化回答。
由于上述背景特征,国内对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并非全然无知,其后在译介、引入和运用更新的西方艺术理论时,同样以自己的方式、渠道和轨迹进行。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与美国汉学在中国艺术领域再度交汇至今,在面对美国汉学(以及其他海外汉学家)的中国艺术研究和诠释话语时,国内学界基本上不是通过他们来对现当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的艺术史观和研究方法进行引入和评估;在判断美国汉学对于中国艺术研究的价值时,即使提及他们的“西方性”“西方特征”或批评其“西方中心主义”,也并未加诸太多笔墨。这也使得美国汉学之中国艺术研究在中国的学术之旅及其影响,迄今还主要存在于围绕具体艺术史、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家问题的观点评估、征引和争鸣;对于美国汉学之中国艺术研究向中国艺术和国内相关研究发出的“提问”,“回答”的方式也主要在这一层面将美国汉学家的观点和成果视为可用于充实对中国艺术之理解的“正读”、有争议甚至需要辩驳的“误读”或可资借鉴的“启发”。
不过,也正由于这一层背景,当中国学术界与美国汉学界同时聚焦于中国艺术这一共同的研究对象和话语载体、在众多的具体艺术史问题研究中展开开放性和创造性的对话时,同样能够呈现艺术史观如何进行横跨“欧亚大陆”的学术旅行,考察其如何通过向中国艺术“提问”而触及被提问者所秉持的中国艺术史观乃至普遍意义上的艺术史观;以及中国艺术又如何在艺术史观和艺术史方法层面反过来向美国汉学界乃至西方艺术史学科“提问”,如何在理论、观念、方法层面成为他们的“问题”。所围绕的中国艺术材料(包括可确认的艺术史现象、艺术家、既存艺术作品和外围相关文献等)大体上可以视为是相对稳定的、主要依靠艺术考古而扩展的物质性客观存在,然而,根据各种不同的艺术史观和文化意识形态,并通过对治史方法的选择、对材料的把握、对事象的记载诠释等,可以充分彰显不同艺术史书写者的观念立场、思维方式、审美个性和创新精神,在丰富的知识生产和开放性的话语表达中凸显根本性的艺术史观问题。
本书从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中所尝试提取的六大“中国艺术问题”,其本质都是围绕艺术史观而问:如何理解艺术史之存在、构成与发展的本质,如何建构或确认对艺术及其历史发展进行认知的思维框架和意识体系,如何通过该框架对艺术史进行分析、归纳和推演,如何形成一定的艺术史叙事话语结构,等等。艺术史观通过这些方面奠定艺术史研究的基础,并向所面对的艺术对象“提问”,认定艺术史问题的来源、范围、性质与内容,并寻求相应的诠释与解答;而新的艺术对象又会对既有的艺术史观加以提问、考验甚至冲击,乃至引出新的问题。史观往往容易在史学研究推进到一定程度后引发学界争鸣,一方面在于史家秉持的史观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治史面貌,另一方面也正缘于这种极具开放性的“提问”与“对答”。虽然当代美国汉学界的中国艺术研究总体上属于一种基于美国学者自身视角的阐发研究,明确发展为一种“比较艺术学”的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范式和案例还很少,但这种区分本身往往也只有相对意义,上述围绕艺术史观的中西跨文化对话与问答始终贯彻其中。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作为一种借身居北美的异域之眼、令视线横跨欧亚的文化旅行,本身就是美国学者们令自身视野不断旅行与扩张、跨过文化时空之间的平行线(而非循着文化之间的相交点而顺藤摸瓜)、触及位于另一平行的文化时空内的对象并与之产生碰撞的过程。旅行者自身的出发点和视野构成方式,最初必然与另一文化时空内的对象形成一种平行的对比框架,以帮助相互间的认识;接触与认识的推进,必然会引起双方相应的心理反应和行为反应,并顺势引发后续的各种言说与行动。这种态势可以视为一种当下的、即时的、交互的、有机的、对话性的相互影响过程,特别是当双方相遇后所凸显的一些问题挑战和考验着自身原本的观念和认知结构、并要求做出调整性的应对之时,更能凸显这些特点。
由于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仍然植根于西方文化思维和认知模式,以现当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的发展作为直接基础,从根本上属于西方学术体制并已形成自身的学术传统,视角来自作为文化空间的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国内学界对于这样一群外来“旅行者”和“他者”的关注点,天然容易倾向于质疑其作为外来者对中国艺术所做阐释和得出的一些问题结论的正确性,关注其研究水平和体现何种程度的西方性(以及由此对中国自身视域内的中国艺术研究所产生的冲击性和挑战性);即使注意到其中的跨文化语境、试图探讨其是否能够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一般也是在前述内容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他们的方法架构和艺术史观念对于中国艺术以及中国艺术研究的适用性和不适用性。这种倾向的根本立场,是认为海外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始终不能真正进入中国“内部”,不能基于真正的“中国经验”思考真正的“中国艺术问题”,充满视域与对象之间的错位和由此导致的误读。但是,跨文化碰撞与交流本质上是一种辩证的双向进程,当来自一种传统的知识分子尝试关注和解释另一传统,其自身的价值和稳定性也必将受到考验,这些关注与解释并不具备只属于一种传统的“纯粹性”。对中国自身而言,西方汉学重新回到中国语境和中国视角时,必然带有从不同语言、文化、思维背景中发明的诸多观念架构和阐释话语;但是,即使当代美国汉学之中国艺术研究的学科基础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还是自“以西释中”的单向阐发轨道延伸而来,也不是仅仅针对中国艺术和中国自身视域内的艺术阐释体系产生单向度刺激,同样也以碰撞中凸显的问题来冲击作为自己立身之本的一些观念、思维和方法,使其方法论演变可以视为西方艺术史学科视野旅行至中国艺术领域、并遭遇和应对一系列新对象和新问题的历程。由此呈现的“中国艺术问题”自然并非固有的、本质化的、未加变形而直接呈现的,而必然是各种语境、历史条件、媒介、理论选择等错综复杂而成的知识建构;它们不能置于某种单一语境下而加以审视,因为它们不仅仅是“关于中国艺术的问题”,更应当视为“中国艺术向他者提出的问题”,乃至“中国艺术为世界而作答的问题”。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也通过其所呈现的中国艺术问题,成为另一种基于中国艺术的创造和意想不到的知识生产,提供了单纯依靠他们自身难以实现的可能性,并最终返回了他们自身:在当代美国汉学的“视觉方法”中,以视觉为中心的内在逻辑和由此提出的视觉自律观念遭遇了来自中国艺术的跨文化检视,并得出了实际上不同于其初衷的结果;中国画学传统的海量文献积累、深厚的图文一体观念、重视文本研究的立场,对现代西方艺术史经典方法中的图文二元对立思维和将文本置于视觉研究的次要地位的观念产生了多方面的挑战;基于潘诺夫斯基经典架构的图像学研究方法和内在理念,还不足以在中国语境中充分回答对于艺术图像的主题、功能、内涵、表达机制和其中人的主体性向度的追问,从而产生对图像学基本框架的各层次进行重构、注意视觉艺术主动表意功能的要求;对于艺术与语境、艺术与审美意识关系问题的解读,既有汉学领域内的独特性,也与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论的整体演变潮流遥相呼应;艺术史家的个人趣味与个性审美问题在现代西方艺术史研究自身的框架中并不彰显,却借助美国汉学家对与自身本质相异的中国艺术的考察诠释而得到了折射。我们也同样能看到,自身观念面对挑战时的捍卫性姿态和开放性姿态,并存于美国汉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中,呈现了认知如何在文明互动中不断产生跳跃与交叠,如何在来自异域的新刺激下尝试告别某一系统下的自我惯性和出现新的生长空间。甚至可以说,在这个作为文化和艺术交流空间的“欧亚大陆”中,处于亚洲(东方)一端的中国艺术也塑造了欧洲/欧美(西方)一端的行动。
所以,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以及对这种研究所展开的考察,其价值衡量标准和本质属性都不在于正确性或水平,而是其如何作为一种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包括通常所说的语言和所谓“艺术语言”——艺术领域的各种形式、符号、语汇等)、跨学科的交往和旅行而存在,其中的机制如何运作,以及对于推进不同文化与艺术的普遍联系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种交往和旅行对于双方的异质性——作为考察者的美国汉学家所持有的思维、观念、概念、范畴、术语,所熟悉的视觉形式构成和运作机制等,都脱离了原本熟悉的西方环境,进入一个相对陌生的视觉世界、语言世界和艺术文化观念世界,而对于受到关注的中国艺术而言也遭遇了陌生的观察视野和诠释架构;可以从中看到这种交往和旅行的跨越性——通过各种多元的动态反应、调整、互适与耦合,中西艺术与文化设法在一定的研究阐释架构内达成两相适应的状态。从研究和旅行主体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认知和理解背景的西方艺术体验与观念、作为当下认知对象的异质的中国艺术如何为他们造就充满碰撞与交流的非常体验,他们的言说必然基于并寄寓这种体验,以及通过他们的接受策略和表达策略等折射出其主体性;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始终没有(也不可能)身处纯粹的西方或中国艺术文化领域,而必然永远动态地处于异质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其所发出的艺术言说永远是中西交流形成的一种“中介语”(interlanguage)。
不过,正是这种“中介语”,以及由此反映的各种相互接触、译介、展览、传播、考察、研究、阐释等艺术交往实践,促使“国别艺术史”“区域艺术史”向更深层次的“世界艺术史”移动与转化,跨越了原本以国家、民族与区域划分的视觉领域界限、语言界限和文化界限,乃至于跨越了艺术与文化思维观念、诗学观念等的学科界限,使中西艺术有可能围绕人类共同追索的问题而逐步衔接成某种整体;也使跨文化的艺术研究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文化、世界文明、世界眼光的具体表现,这种研究实践和文化艺术旅行的历史成为一种世界历史,即世界艺术的全球性相互接受与交相熔铸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美国汉学的中国艺术研究应当被视为一个中西哲学、美学、艺术文化观念相互交流、碰撞、调整的过程,我们可以经由两种文化的砥砺互动,在更加深入地把握中西艺术文化观念内涵、相互反观各自的艺术文化构造取向的基础上,寻求对艺术问题所反映的人文学科特质及其内部关系的更深理解。而通向更深理解的道路,始终以双方的交汇与对话为路基。如此,必能为中国艺术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艺术”与“世界知识”的可能道路提供重要的借鉴参考。
- 当前位置:首页 > 通知公告